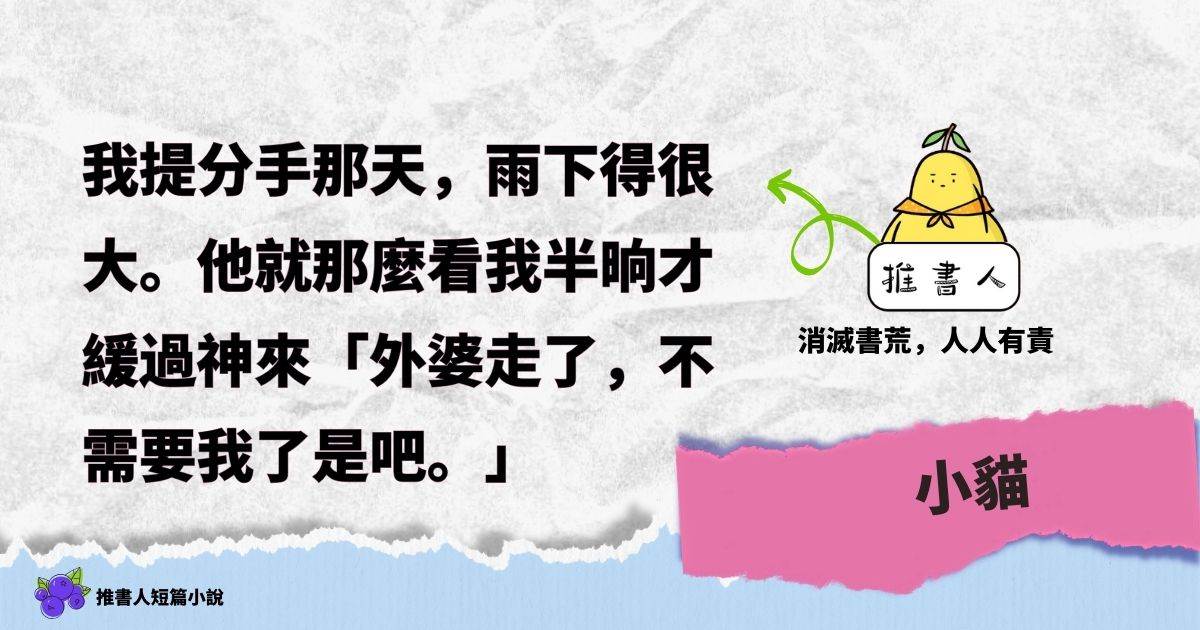《小貓》第4章
后來當我知道外婆怕我驚醒,守著我一夜沒睡時,再碰到下雨天,無論雷聲多麼響,我再也沒害怕過。
大概是從小就告訴自己要堅強,所以我膽子其實挺大的。
推開辦公室的門,我沒想到看見的是張姐。
她抬頭看見我,顯然也是一驚。
「何描?」
我聽同事說起過,她這幾天跟姐夫吵架吵得厲害,想必是因為這件事,一個人偷偷躲在這里抹眼淚。
我并不算會說話的,安慰人也不知道從何說起,只能學著同事們的模樣勸她:「張姐,沒有夫妻是不吵架的,聽說姐夫以前也是咱們臺里的,你們很恩愛,不要因為一時意氣而爭個高低互不相讓。」
張姐聽著我的話頻頻搖頭,我知道這些話沒什麼說服力,她大抵也是沒聽進去。
果然,我不擅長說好話。
「小何,我不知道這些話該跟誰說,真的難以啟齒。」
我知道,她打算跟我說些心里話,于是拉了把椅子坐在她旁邊,想著一會無論她說什麼,我總要好好勸勸。
但她開口,就打得我一個措不及防。
「你姐夫他,從前不是這樣的,自從他染上賭博,好像變了個人一樣,為什麼?」
賭博?
這兩個字好像已經離我很遙遠了呢。
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那個人了。
「不是變了個人,賭徒根本不是人。」
張姐抬頭詫異地看著我,而我原本準備好安慰她的話再說不出一個字。
8
回家的路上,在街邊吹了近一個小時的冷風,我才讓自己重新清醒。
逼迫自己想一些明天要做的事和工作安排。
才強行將那些窒息的回憶給壓了下去。
我租的小區已經很老了,伴隨著年久失修和無人清理的垃圾味道。
但這是我目前能找到離公司最近,最便宜的地方。
這里基本住著一些無業游民或者是啃老本兒的,鮮少有車輛出入。
所以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停在我家樓下,那輛看起來和這里格格不入的豪車。
盛成周靠著車窗站在那里,手里夾著的煙明明滅滅的。
那天他那句帶有嘲諷意味的「何小姐記性可真好」還回蕩在耳邊。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沒有什麼失憶,他就是故意那麼說的。
他轉頭看見了我,又回過頭去,吸了一口然后掐滅煙頭,吐出一個濃重的煙圈。
「下班這麼晚?」
他的聲音有些喑啞,我瞄了一眼,地上至少有四五個煙頭,不知道他在這里站了多久。
我整理了思緒,然后換上得體的笑顏:「盛總,好巧。」
他卻連裝都懶得再裝,冷哼了一聲:「把面具摘了跟我說話。」
我從前不是這樣的,大概七八歲的時候,我就不覺得自己是個小孩子了,那些整天圍繞在身邊嘰嘰喳喳的同學只會讓我覺得厭煩。
青春期更是沒有過,那些什麼少男少女的春心萌動,在我看來就是浪費時間浪費精力。
在所有人眼里,形容我的詞最多的就是冷漠。
我不在意,每天只會悶頭讀書,我只想拿獎學金,畢業后找個好工作,讓外婆過上好日子。
從不會曲意逢迎,或者假意討好。
我以為只要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但事實不是這樣,步入社會的每一天,我好像都在碰壁中度過。
然后在日積月累之下,學會了戴上面具生活。
盛成周說讓我摘下面具,但我現在沒有那個資格,我想要賺到錢活下去,就要學會假笑。
9
「上樓。」盛成周的語氣不容反駁。
于是他邁進了我那三十來坪堆滿雜物,大概還不如他貓窩的家。
他也不見外,進屋之后就徑自找地方坐下了。
我拿著水壺詢問:「水還是茶?」
「水。」
「哦。」
「我不那麼說,你是不是要一直裝下去?」
盛成周沒來由的一句話讓我不明所以:「什麼?」
他伸手撫了撫額,語氣不太好:「火車。」
噢,如果你不說,我可能會一直裝作不知道吧。
三年前跟他分手后,我怕那個男人找上門來,匆匆休了學,然后去了陌生的城市。
輾轉一年,終于在外婆忌日時決定鼓起勇氣回去。
我是萬萬想不到會在那輛火車上遇到盛成周的。
我一如既往地戴著寬大的口罩,帽檐壓得極低,縮在靠窗的位置假寐。
旁邊不知道什麼時候坐了人,我想起身去廁所,正要開口麻煩他讓一下。
在看到那張臉的時候,慌張地閉上嘴,重新坐了回去。
為了不讓他發現我,我愣是忍著憋了一路,廁所都沒敢上。
我假裝專心給他倒水,狀似無意地問:「你怎麼會在那輛車上?」
以盛成周的性格,那種人擠人又烏煙瘴氣的綠皮車,他是絕對不會坐的。
「你覺得呢。」
我咋舌:「不知道。」
他好像有些氣急敗壞:「我去追債的。」
我看他一眼,追的該不會是我的債吧。
那之后,盛成周就不說話了,我也不知道說什麼,不知不覺兩個人沉默了半個小時。
直到那壺水已經快喝完,盛成周還沒有要走的意思。
我拿起來準備再燒一壺。
他忽然開了口:「那天你請假是躲我嗎?」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