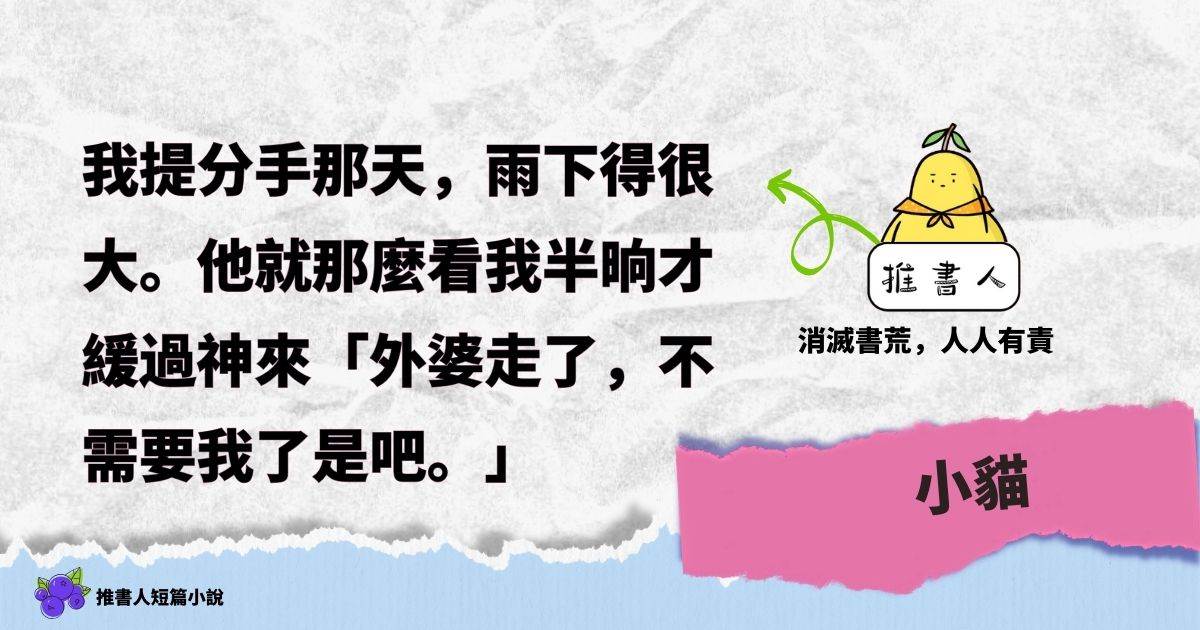《小貓》第2章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他說出小貓那兩個字的時候,好像加重了語氣。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認出我,看樣子是沒有的,或許他早就不記得我了。
但我不行,我忘不掉。
「對不起先生,我只是個實習生,沒有門禁卡,既然下來了,我沒辦法帶您上去,您可以明天白天來找找看。」
我感覺他的視線一直落在我頭頂,半晌輕輕嗯了聲。
我靜靜等著,但半天他也沒有讓出去路的意思。
抬頭的瞬間,又一次和他對上視線。
他的表情依舊從容得很:「您貴姓?」
我甚至能感覺到自己心臟撲通撲通越跳越快的節奏。
聲音小得細如蚊蠅:「我姓何。」
「何小姐。」他皺了下眉頭,「我們是不是在哪里見過?」
說著他好像還認真回憶了下,我心里苦澀,雖然口罩遮住了我大半張臉,但是距離這麼近,眼神對上的瞬間,他都沒有認出我。
他,果然已經不記得了。
大概是看出我的尷尬無措,他不置可否地笑了下:「兩年前我曾坐火車去出差,回去時出了場車禍,很多以前的事都有些模糊了。
「抱歉,實在是看您覺得眼熟,所以才冒昧地問了,不會給您造成什麼困擾吧?」
車禍?
幾乎是下意識脫口而出:「怎麼會這樣,嚴重嗎?」
許是我的語氣過于關切,他的神色頓了頓。
我趕緊斂了心緒,狀似平常:「兩年前我也曾坐火車回過老家,那時候您的位置在我旁邊,應該就是那時候見過吧。」
我自覺說得沒有什麼遺漏,既然他已經忘了,那,也好。
聞言,他卻忽地笑了下:「何小姐,您的記性可真好。
」
然后在我詫異的神情下,他的目光逐漸冷冽,轉身離去。
4
兩年前,那是我時隔很久終于鼓起勇氣踏上了回到老家的列車。
那天是外婆的忌日。
自從外婆去世后,我匆匆休了學,輾轉了好幾個城市。
再也沒有了從前認識的人的任何消息。
我整日將自己隱匿于寬大的口罩之下,就怕某一天那個吸血鬼一樣的男人面目猙獰地來到我面前,不顧一切地嚷嚷著:「何描,你個小賤人,趕緊把錢都給我交出來。」
從我出生起便是一個不幸,母親難產,父親見生下的是個女兒,頭也不回地就走了。
若是沒有外婆,我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何方,甚至能不能活著。
是外婆到醫院親自把我抱回了家。
她說:「我們阿描才不是沒人要的小孩。」
就這樣,她一個孤寡老人拖著我一個沒人要的小孩,一養就是十九年。
我深知自己家境不好,外婆一個人養我也甚是艱難,所以我只能拼命學習,一次一次地拿回獎學金。
外婆身體日漸不好時,我束手無策,能做的還是只有不停地學習,我只能期望著自己得到的獎學金越來越多。
大一那年,外婆在家里摔了一跤,身體狀況急轉直下,醫生下了最后通牒,說兩個月內必須要做手術,保守的藥物治療已經不管用了。
接到消息的時候,我拿著自己三百塊錢買的二手手機,顧不上周圍同學異樣的目光,直接沖出教室奔去了火車站。
正值五一假期,當售票員告訴我近三天都沒有票了的時候。
我終于再也忍不住,躲在售票大廳外的柱子下失聲痛哭。
這就是沒有錢的悲哀。
連最便宜的火車票我都買不到。
不知過了多久,眼淚好像流干了,我坐在那里發愣。
盛成周就是這時候過來的。
他蹲下身,低到跟我平齊的位置。
他說:「何描,我帶你回家。」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飛機,我才知道,原來這里到我家,只需要一個半小時的路程。
下了飛機還要繼續坐兩個小時的客車才能到我家的小鎮。
在客車上,我明顯感覺旁邊的盛成周身體不適,眉頭緊鎖,他這種人,大概一輩子也沒坐過這麼破又顛的車吧。
外婆在病房里靜靜地躺著,她看上去精神還不錯,見到盛成周還笑著招呼他:「是阿描的同學吧,過來坐,辛苦你還陪她跑這一趟。」
在病房里陪了外婆半晌,直到她精神不濟沉沉睡去,我才去找了她的主治醫生。
當得知手術費需要三十萬的時候,我的大腦空白了一下。
三十萬,好像是我這輩子都觸及不到的數字。
但盛成周不一樣,三十萬對他來說不足掛齒。
在外婆強烈要求下,我帶他去吃了醫院附近的盒飯。
他坐在那里一口都沒有動,我覺得感激又對不住他:「謝謝你,機票的錢以后我會還給你,這里的菜不好吃,回去后我請你吃飯吧。」
他依舊沒有動,卻像是考慮了很久才答非所問:「何描,如果我能支付你外婆的醫藥費,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嗎?」
5
我跟盛成周同班,但交集并不多。
剛開學的時候,他坐我后排的位置,我聽見他跟身邊的人說話:「剛看了一眼,榜上好像有個叫何貓的,這名字有意思。
」
我坐在前面一言不發。
后來同學都熟悉之后,他還特意跟我來解釋:「不好意思何描,剛開學那天我還誤以為你叫何貓,你聽到了吧?」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