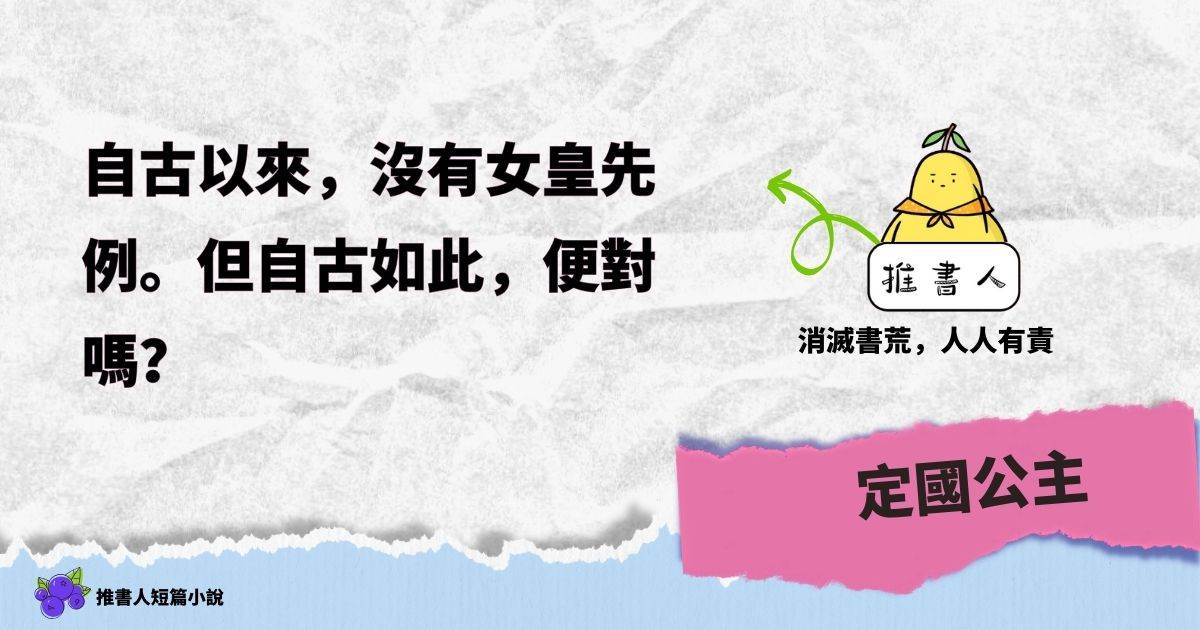《定國公主》第5章
我笑起來:「陛下說什麼,為國為民盡一份力,這是臣妹的福分。」
蕭昱大概想不到我如此順從,但無論怎麼樣,他對我的識相都很滿意,然后他說:
「皇妹,沒想到你如此識大體,那明日早朝,就請你自己請辭前往塞外吧。」
我笑了。
他想趕走我,又不想落得個賣妹昏庸的名聲。
我想也怪不得我父皇在這三位皇子中猶豫那麼久。
我直視他,直到他在我目光下偏過視線,我才說:「臣妹,遵旨。」
大概是我要走了,皇兄沒有吝嗇對我的贊揚,整個衛國的百姓都知道他們的定國公主深明大義,不僅在塞外守護邊疆,逼得犬戎寸步難進,還為了國家休養生息,主動愿意去和親。
歌頌我的戲折子演了一出又一出。
當然也有人疑惑大捷在即,為什麼要讓定國公主去蠻夷和親,關于蕭昱嫉恨我的流言從青樓瓦角在口口中隱晦的流傳。
只有蕭昱不知道,他沉浸在送走我的喜悅中。
可能是我要走了,他也不裝了。
我想我將永遠記得他跟我說的這些話:
「皇妹,不要怪我,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從小到大,你樣樣比我強。」
「我知道父皇最后立我還有考量你輔政的角度。」
「可是越這樣,我越恨。」
「你看如今,你再有才又能怎麼樣?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我要你知道,我是你的君。」
「我要你如何你就只能如何,你這輩子,都越不過去我知道嗎?」
「你要怨,就怨母后沒有將你生成男兒身。」
我一句話都沒說。
外面吵得沸反盈天,我一直待在我的行宮里,足不出戶。
直到要出發和親前,行宮來了一位故人。
新科狀元,宋淼。
他就是當年那個花魁的情郎,我殺了王炎后,給他換了一個戶籍,讓他參與科舉。
他倒也沒辜負我,做的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好。
他跪在地上,恭敬肅穆的朝我行了三個大禮。
我泰然處之的受了,我說:「宋淼,我有件事要交代你。」
他抬起頭,沉默寡言的一張臉,他說:「萬死不辭。」
我笑起來。
坐上去往犬戎的轎子的時候,我看見皇兄嘴角的笑。
他大概第一次對我笑的這樣愉悅和真心實意。
我想他大概是覺得這一輩子都不會再看見我了,在臨行前倒生出一點依依不舍來,囑托我:「阿鳶,萬事小心。」
他也知道讓我小心,我和犬戎打了兩年的戰,此次去犬戎,不被生扒活吞,離被折磨也不遠。
我笑,在上轎前回頭望了這偌大的皇宮一眼,夕陽西下,最后的一抹余輝斜射在金色的琉璃瓦上,熠熠生輝。
我收回目光,含笑看著眼前的蕭昱,他不知道,我一定會回來。
不是我想,是我一定會回來。
送親的隊伍在大野澤被軍隊攔了下來,齊行之帶著嚴陣以待的將士攔在我去犬戎的路上。
我撩開轎簾下來的時候,他帶兵一動不動的站在冬雪里。
我在塞外兩年,我們一開始針鋒相對,到后面成為生死與共的戰友。
我們一起在寒冬的天里吃過凍的僵硬的饅頭,一起在篝火的火光中痛飲過烈酒。
我從犬戎的包圍里救過他,他也在死人堆里扒出過我,歲月將他沉淀出殺伐果斷的堅毅,此刻他面無表情的橫槍立在我面前,他身后的將士也是一臉肅殺。
目光流轉,一句「你瘋了」被我噎進嗓子里,我頓了頓,笑起來:「你是來送我?」
他看著我,面無表情的問:「你想去嗎?」
他一直在等我的回答,我相信如果我嘴里說出一個不字,他會立馬將我攔下,然后揮兵犬戎,再進京向我皇兄告罪。
我看著他:「我會回來的。」
他定定的看著我,常年的配合作戰讓我們默契,我想他一定能明白我的用意。
我會回來的,只是現在時機不對,我也不會讓跟我一起出生入死、并肩作戰的兄弟們背上叛國的污名。
我需要齊行之幫我做更重要的事。
他頓了頓,讓開了一條路。
他身后的將士低聲喚:「將軍。」
他抬手向后招了招,列陣的陣營退往兩邊,漸漸讓出一條通道來。
我閉上眼頓了頓,然后轉身上了轎。
送親的隊伍一點點往前,我聽見轎外有人低低的唱起送別歌,低沉渾厚,帶著蒼茫遼闊的悲哀,漸漸匯聚成一團: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豈曰無衣,與子偕行。
等我回來的那天,將沒有任何人再能支配我的命運。
6
我是衛國建國以來,第一位遠嫁和親后,還能回來的公主。
我回來的那日,整個衛國歡天喜地,百姓十里迎拜,我阿兄率領群臣親自站在承乾門接我。
從馬車上下來的時候,他看著我紅了眼,說:「阿鳶。」
我似笑非笑的望著他,默不作聲。
他這樣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大概是以為我在犬戎遭了大罪,但我知道他心里的快活。
我越慘,他就越開心。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