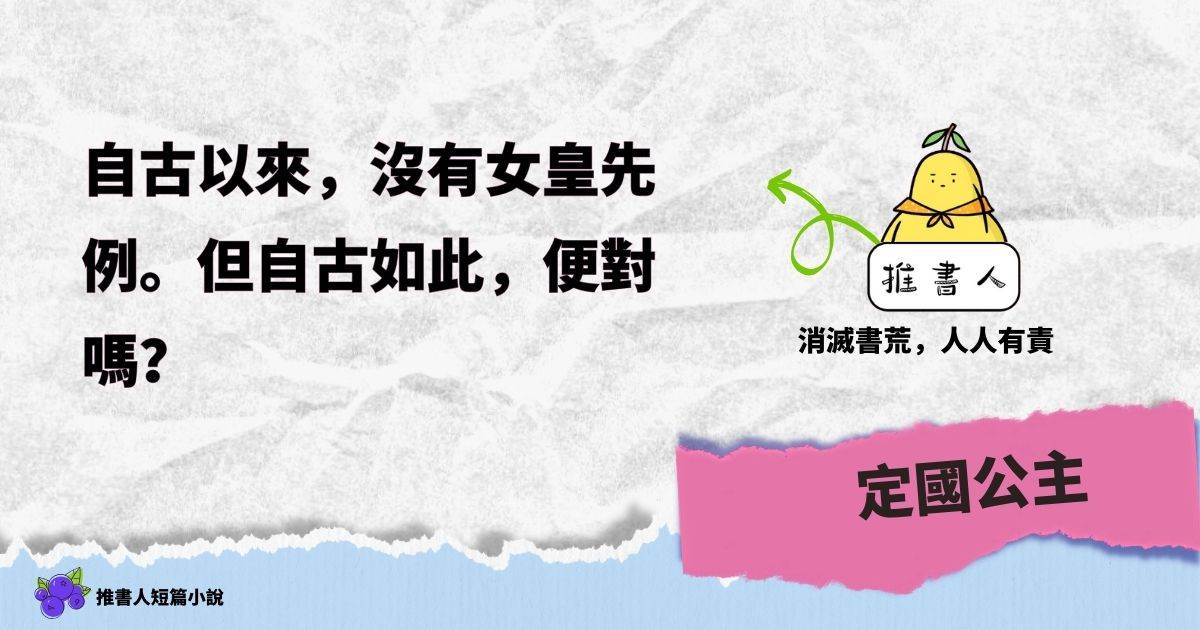《定國公主》第1章
和親回來后,皇兄問我:「阿鳶,你想要什麼?」
我似笑非笑看著他身下的龍椅:「皇兄這把椅子真漂亮。」
皇兄笑起來,第二個月就讓內務府打造一把一模一樣的椅子送過來。
只是為了不逾矩,兩側的龍雕換成了蛟。
我摸著那把椅子目光深邃。
皇兄以為我想要這椅子。
他不知道,我想要的,是這椅子下的皇位。
1
我是衛國建國以來,第一位以才德聞名朝野的公主。
我過目不忘,三歲識字,六歲那年父皇設宴,宴上讓幾個兄長姊妹以「新月」為題寫詩,我蘸酒在桌子上寫下:
「初月如弓未上弦,分明掛在碧霄邊。時人莫道蛾眉小,三五團圓照滿天。」
父皇大笑,后來就時常調侃我的幾位皇兄,沒有一位才華比的上我。
八歲那年,我和教導我的太傅弈棋,廝殺到最后太傅額上都出了汗,最后險勝我半子。
父皇看出我讓棋,意味深長的說:「阿鳶慧心巧思,難得還懂謙恭下士,不露圭角,你的三位皇兄都比不上你。」
我三位皇兄聽了這話也不惱,只是笑嘻嘻的望著我,順著父皇的意思稱贊我。
他們知道,即使再優秀,我也不會對他們造成任何威脅。
因為我只是位公主。
再令父皇寵愛滿意,以后也是要嫁人的。
后來父皇開始挑選太子。
對于一個帝王來說,父皇的后宮其實并不算充實,所以連帶著子嗣亦不算多。
我只有三位兄長,兩位姊妹。
可就是這三位兄長,父皇猶豫數年都沒確定下太子人選。
大皇兄有勇力,但暴戾恣睢,個性獨斷。
二皇兄性子優柔寡斷,生母又地位底下。
三皇兄才德尚可,只是鋒芒不露,沒有帝王胸懷。
我記得父皇時常望著我嘆息,遺憾說:「阿鳶秀出班行,只可惜不是男兒身。」
當時左右無人,我問父皇:「女兒身不行嗎?」
「自古以來,沒有先例。」
「自古如此,便對嗎?」
父皇沒有動怒,只是溫和的摸著我的發頂,目光落在虛空中:「這個問題的答案,要你以后自己去找了。」
我就不說話了,父皇可以說是衛國建國以來最圣明博學的君主,他都不確定,那我就只能自己去找答案。
2
太子人選最終還是定了下來。
和我一母同胞的三皇兄——蕭昱。
定下太子之位那天,父皇領著阿兄站在我面前,看著我說:「阿鳶,以后你要扶持你的兄長。」
「你們一母同胞,感情深厚,有你在你皇兄身邊,父皇就放心了。」
我在阿兄殷切的目光中點了點頭。
后來父皇就將我的稱號改成了定國公主。
定國定國,其中的寓意不言而喻。
我其實沒想過和阿兄爭皇位。
我們的感情很好——曾經。
他得了什麼新奇的東西都會先拿過來讓我挑。
小時候我失足落水,他想都沒想就跳下去撈我,等下了水他才想起,他自己也不會鳧水。
那次把母后嚇得夠嗆,心悸了數月才恢復過來。
「你是不是傻,周圍都是人,你喊一聲就行,何必自己跳下去,要是你和阿鳶一起出事,讓為娘可怎麼辦?」
阿兄一邊擦頭上的水,一邊笑:「當時沒想那麼多。」
后來十四歲那年,父皇沒有征兆急疾大薨。
當時南方洪澇,阿兄領旨正在江南一帶賑災。
大皇兄手握重兵,對著紫禁城虎視眈眈。
母后六神無主,除了哭什麼都不知道。
是我當機立斷,派人封鎖太醫院,確保任何消息都傳不出去,然后讓死士從角樓出去,快馬加鞭去通知阿兄趕緊回來。
為了保險起見,我還將遺詔和玉璽藏在只有我和阿兄知道的地方。
這樣即使大皇兄逼宮,沒有遺詔和玉璽,他永遠都名不正言不順。
我用盡一切辦法將父皇的死訊拖延了整整了八天,只說是生病。
為了鞏固國本,不至于上演兄弟鬩墻的局面,我還大逆不道讓父皇的遺體躺在冰床上。
最后大皇兄心生疑惑,沖進紫宸宮,用劍架在我的脖子上,讓我將父皇交出來。
我神色不變,冷靜地望著大皇兄,甚至微微笑了笑:「大皇兄,父皇需要靜養,等他清醒過來,看見你這個樣子,不知道該有多傷心。」
頓了頓,我補充一句:「不過我理解大皇兄此舉只是因為擔心父皇,百善孝為先,想必父皇也理解。」
恰好一陣風過,將身后的帷幔拂起一角,又輕飄飄的落下,父皇閉眼的臉一閃而過,離得遠,大皇兄看的不真切。
但他到底是猶豫了,我又鎮定自若,在大皇兄狐疑的目光中兩指夾著劍鋒,他半推半就順著我的力道放下手里的劍。
我又為阿兄拖延了兩日。
直到大皇兄破釜沉舟,帶人沖進來,阿兄已經穿著孝服從紫宸宮后榻踱步出來,看著大皇兄笑起來,不動聲色的說:「兄長這是做什麼?」
大局已定。
后來大皇兄以謀反罪名被囚允州,臨行前他對我阿兄說:「蕭昱,我不是不如你,我只是沒有一個蕭鳶這樣的親妹子。
」
阿兄眼皮未抬,笑:「有阿鳶,是我之幸,你之不幸。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