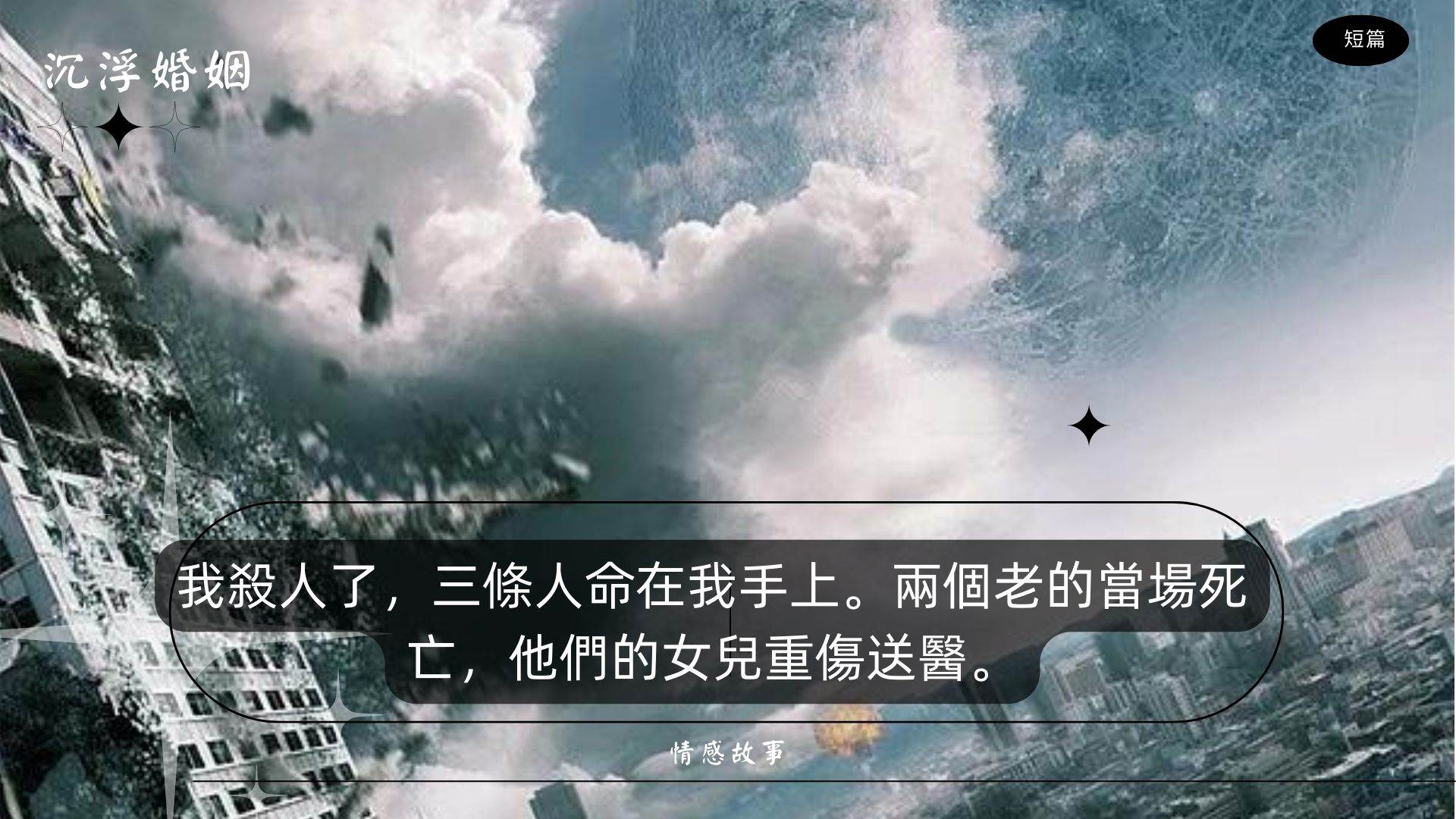《太陽照不到的地方》第3章
只能用手壓著,吃力地看著。
“只有血才洗得掉名譽上的污點。”
污點,是誰的污點呢?
我問獄警想要一只筆,被拒絕了,他們大概擔心我自殺吧。
我怎麼舍得自殺呢?
光明才開始啊。
不出一天,警察又來找我了。
我無奈地放下書,被獄警帶了出來。
還是上一次的那兩位。
我觀察了一下,胡子更長了,眼圈更深了,就連玻璃杯的茶葉放得也更多了。
看樣子,案件進行得不順利。
年輕警察少了很多的戾氣,他的語氣只有深深的挫敗:“我們深度調查了你和周家人五年來的相處。走訪了鄰居、家政中介……他們對周家二老的為人都給出了肯定的答復。至于你們的關系,從所有人的口中得知,確實很和諧。”
他頓了一下:“所以,你是估計在給受害者污名化嗎?這樣并不能讓你減刑。”
我比他更無奈,怎麼到現在還覺得我需要減刑呢,他看不懂我眼里的視死如歸嗎?
于是,我挑釁他:“我不在乎減刑與否,如果可以的話,明天執行死刑我也樂于接受。但是你們……不舍得啊。”
“你……”他的情緒又上來了,像一個火藥桶,一點就爆。
還是年長的警察有經驗,他喝了一口濃濃的茶葉水,把不小心吃到的茶葉吐了出去。
“說吧,你到底想要什麼?我們會盡可*W*W*Y能的滿足你。”
和聰明人對話,就是省力。
他繼續說著:“我相信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但是孩子是無辜的,我們還是希望能……”
我也不裝了,鎮定地說:“我要周曉婷來見我。”
老警察也為難了:“這個……你知道的,周曉婷還在醫院,她的傷勢不輕。
”
我微笑地說道:“我當然知道,可是她受得都是硬傷,只要不出血過多,就不會致命。我下手的時候,注意輕重的。”
年輕警察忍不住了,罵罵咧咧:“媽的,瘋子,都是瘋子。”xʟ
周曉婷如約來見我。
幾天不見,驕傲恣意的她已經徹底變成一個虛弱的怨婦。
怨的家破人亡,更怨——自己從此以后只能在輪椅上度日。
推她進來的是杜思遠,她再也沒有可能嫁的男人。
周曉婷看見我的時候,好像見了惡鬼。
她的眼里有仇恨,但是更多的是害怕。
我好好地欣賞了一番。
首先開口的是杜思遠。
他冷靜自若:“江女士,我不知道曉婷家到底和你有什麼過節,但是小寶還小,她甚至都不怎麼回國。她外公外婆做的事真的和她無關,希望你能網開一面。”
我饒有興致地聽完了他的論述,朝著他吹了聲口哨:“帥哥,我什麼時候說過,我和周家二老有過節?”
“那你為什麼殺他們?”說話的是周曉婷,她淚流滿面,憤恨至極。
我死死盯著她的眼睛:“因為我的仇人是你啊,曉婷。”
5
周曉婷驚恐地看著我:“我根本不認識你?”
我沒有理睬她,繼續笑著吹著口哨,旋律是十多年前京海一中風靡的一首歌。
當時的軍訓篝火晚會上,校長傾情演唱了這首《漫漫人生路》,后來一度成為了我們的校歌。
但是可惜,周曉婷還是沒有反應過來。
她期期艾艾地求著我:“醫生說,我這輩子只能坐輪椅了。這樣,能否消減你的仇恨,求你告訴我們,小寶在哪里?”
杜思遠也說:“江女士,我們活要見人、死要見尸。
求你體諒一下做父母的心情。”
我翻著眼睛思索了一下:“誰說那個小孩死了。現在還沒死呢,不過過幾天就不一定了。”
杜思遠一下子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看不出來,這種富二代還是個女兒奴。
“你想要什麼?要諒解書嗎?我們立馬寫。錢也可以,你盡管開口。”
“我要的很簡單,但是就怕你們給不起。”
杜思遠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你盡管說,我們杜家會盡量滿足的。”
聽到這話,我笑得左搖右擺,隨后指了指周曉婷:“我要她給我跪下。”
周曉婷一愣,咬牙切齒地看著我,從牙關里蹦出幾個字:“你在耍我們。”
我誠懇地說:“沒有,我就是想看你跪。”
她再也忍不住,爆了粗口:“賤人,我這腿怎麼跪?”
她的腿上甚至還包著紗布。
“那是你的事。”我冷漠地看著她和杜思遠,“不跪,*W*W*Y我憑什麼放了你女兒,不過也就是一條命而已。”
杜思遠很上路子。
他與我對視良久,突然伸手把周曉婷從輪椅上提了起來。
周曉婷尖叫起來:“思遠,你干嗎?!”
杜思遠像是沒聽見一般,用腳把輪椅往后推了一下。
然后把周曉婷放在了地上,唯一有良心的一點,他是輕輕放的。
但是周曉婷的雙腿遭了罪,血跡從紗布上滲了出來。
她慘叫著,把獄警都嚇了一跳,趕緊叫了醫生過來。
“可以了嗎?”杜思遠冷冷地問我,“跪了,五體投地。”
我很欣賞他:“當然可以,很有誠意。今天晚上7點,讓你妻子和我連線直播,我會在直播里告訴你們孩子的地點。哦,不好意思,她還不是你的妻子。”
周曉婷被重新扶上了輪椅,醫生要推她去進行消毒治療。
但她不愿意,非得和我對峙著。
就像現在,聽到直播,她又開始鬧起來:“憑什麼,你說什麼我就要答應你嗎?你這個騙子,我跪也跪了,孩子呢?”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