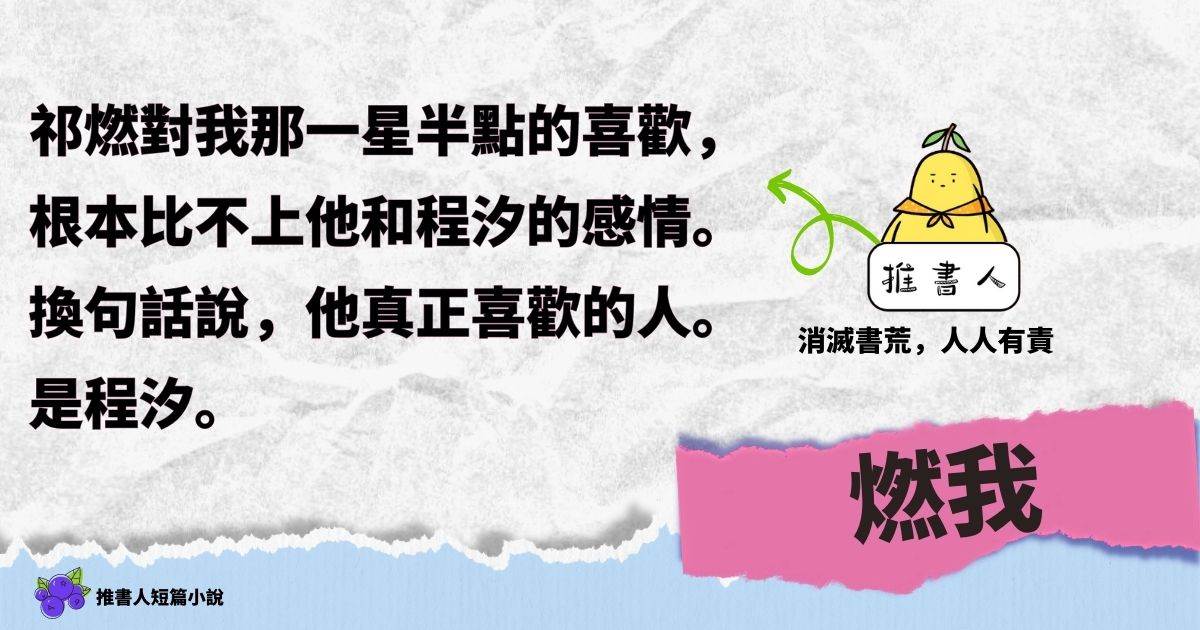《燃我》第6章
但在警察找到前,我還不得不忍受他的變態行為。
「渺渺,蛋糕好吃嗎?」
「這是我第一次做。」
祁燃從身后攏住我,切蛋糕的刀放在我腿上。
他拿著勺子一口一口地喂我。
冰涼的刀片貼著我的腿,我甚至不敢顫抖。
「我問,好吃嗎?」
他第二遍的發問依舊帶著笑意,卻隱隱不耐煩。
祁燃指尖撥弄了一下我腿上的刀,讓它轉了個方向。
正對著我。
警告意味十足。
「嗯……」
我味同嚼蠟,含糊應了一聲。
但祁燃因此愉悅了不少。
拿走了我腿上的刀,把我抱得更緊了一些。
他靠近我的耳邊,低聲呢喃了一句外文。
祁燃說這是意大利語。
是《美麗人生》里的臺詞。
我皺眉回想這部黑色幽默的電影,卻根本想不起現在的場景,能跟里面哪句話聯系起來。
我沒心情糾結這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因為已經近乎凌晨。
該考慮睡在哪里了。
祁燃抱著我走到床邊,把我扔上去。
他垂眸盯著我,解著外套的扣子。
「祁燃,我說真的,你最好別逼我。」
我后退躲在床角。
祁燃挑眉輕笑。
「輕松點兒渺渺,我倒也不至于那麼畜生。」
同一張床上。
他只是躺在我旁邊,手搭在我腰上。
我板著身子,一動不動。
旁邊的祁燃驀然睜眼。
「渺渺,你是要我哄你睡嗎?」
他搭在我腰上的手有上移的趨勢。
我登時閉上眼,強迫自己忽略掉旁邊的氣息,逼著自己入睡。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警惕中醒來。
腳腕手腕被捆著一晚上,血液有些不流通。
這是我唯一自救的機會。
「祁燃。」
這是近幾個月來,我第一次用這麼溫和的聲音跟他說話。
我抬頭看著他,隱隱透著哭腔。
「你綁得我手腳都疼了。」
「給我松松吧,好不好?」
祁燃怔住,看了我幾秒沒說話。
似乎在判斷真偽。
「渺渺……」
對視良久,他似是妥協,俯身給我解開絲巾。
我稍稍活動了下手腳。
余光注視著祁燃。
他緊緊盯著我。
片刻后,見我沒有要跑的意圖,便放下了警惕。
我就是這時,猝不及防逃跑的。
祁燃個子高,腿長。
我只有拼命往前跑,才有一線生機。
身后腳步聲越來越近。
我終于碰到大門,一拉。
我撞進了人的懷里。
下一秒,我就被捫進了懷里。
「段思渺。」
陳烆身上熟悉的氣息,讓我瞬間卸了力。
男生沉著臉把我翻過來轉過去地檢查。
「他打你了?」
我搖搖頭,「我沒事。」
祁燃靜靜地站在我們身后,神情沒有一絲波瀾。
「渺渺。」他再度開口。
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一場暴風雨后的告別。
不遠處已經隱隱傳來警笛聲。
陳烆一言不發地把我推出門去,反手關上了門。
在警車停在別墅門口那一刻。
門被打開。
陳烆表情淡淡。
我越過他去看祁燃。
男生坐在沙發上,顴骨處帶著明顯的傷痕。
他平靜地坐在那里,沒有再抬頭一次。
14
16 歲以上就要承擔刑事責任了。
祁燃的結局,我沒再過問。
主要原因是陳烆陰陽怪氣得不行。
「你不就想問那孫子怎麼判了嗎,有話就說。」
他垂眸掃了一眼我的欲言又止,冷嗤一聲。
我憋了半天,才問。
「我其實想問,為什麼那天祁燃臉上有傷,你沒有。是因為他一點也打不過你嗎?」
陳烆挑了挑眉,模棱兩可。
「我也沒給他動手的機會。」
我了然,并對男朋友表示欽佩。
但作為男朋友的陳烆反過來嫌棄我。
他認為,我之所以能被祁燃帶走。
除了祁燃是個死變態這個原因外,也因為我不夠強大。
由此,陳烆提出教我散打。
「……不要。」我漠著臉拒絕他。
「為什麼?」
直男不解。
我懶得理他,扭頭就走。
陳烆雖然不能理解,但格外尊重我。
談戀愛這幾年來,我不喜歡的事,很少勉強。
當然,也有例外。
比如大學開始,生理期的時候,我就會異常排斥陳烆。
而且,只排斥他。
「離我遠一點,謝謝。」
「我求你了,我想自己一個人待一會兒。」
陳烆氣笑了,「我什麼都沒干也不行?」
「對,就很煩你,看到你就煩的程度。」
陳烆抵了抵牙根,冷哂一聲,朝我走過來。
兩只手撈著衣擺,就把套頭衛衣脫了下來。
「你干嘛啊!」我格外脾氣大。
陳烆走到床邊,圈住我的腳踝,往他面前一拽。
男生壓了上來。
「慣的你。」
話音剛落,他就力道很重地吻了下來。
但礙于生理期,陳烆什麼也做不了。
親著親著,他就停了下來。
微抬起身看著我。
「段思渺。」
「這是我們認識的第十一年。」
我輕嗯了一聲。
腦海里回憶了一遍陳烆這十年來的變化。
然后,我聽到 22 歲的陳烆說。
「段思渺,結婚吧。」
我想起他第一次告白的樣子,用他曾經的話回他。
「陳烆,有點儀式感。」
很久以后,我回想起當年那場盛大的求婚,都會在回憶里一次又一次地震撼。
15(祁燃視角)
我被放出來后,沒再回學校。
程汐來看過我一次。
但她人連著輪椅,都被我從二樓扔進了泳池。
看著她被司機撈起來時狼狽的樣子,我愈發礙眼。
「怎麼就沒死呢?」我閑閑地笑著。
程汐不顧一身落湯雞的樣子,沖著我嚷。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